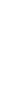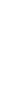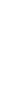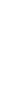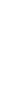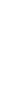战地摄影师手札 - 第2002章 天下太平
第2002章 天下太平
仍旧残存着侵略和反侵略战争痕迹的残破长城上,卫燃努力将相机举的更加平稳一些,艰难的用取景窗套住了那对没有喜悦只有悲伤的新人。
然而,还没等他按下快门,不远处的台阶却走上来一个金发女人。
她穿着棕色的厚实风衣,胸口挂着一台依康塔照相机和一台超级依康塔,肩头还挎着一个帆布包。
不止于此,在她的怀里,还有个长相可爱,混血样貌的小丫头,这小丫头的手里,更是拿着一张董维新的照片。
“艾米?”卫燃错愕的看着对方,很是反应了一下这才将其认出来。
“卫燃同志”
艾米的语气中并没有久别重逢的喜悦,她甚至格外的平静,“真好,你们的战争结束了,你还活着。”
说着,她扭头看向了并排站着的赵守宪和王以沫,近乎笃定的说道,“你们就是赵守宪和王以沫吧?我是董艾米,董维新的妻子。
如果你们把维新当做大哥,那我就是你们的嫂子,如果你们把他当作叔叔,那我就是你们的婶婶。”
“婶婶婶”
赵守宪和王以沫反应过来,恭恭敬敬的打了声招呼,同时也下意识的看向身后,“董董小叔叔呢?他.”
“他死了,早就死了。”
艾米,不,董艾米苦涩的笑了笑,“1947年的10月他就死了,他当时潜伏在长春,他他暴露了。在被抓前,他给我发了一封电报,让我”
用力做了个深呼吸,董艾米搂紧了怀里的孩子,“让我在战争结束之后,来喜峰口参加婚礼,送上贺礼,替他喝一大碗喜酒。”
说着,董艾米将手伸进挎包,从里面拿出了一个带着浓厚包浆,而且拴着一把鱼儿刀的酒葫芦递给了不知所措的赵守宪,“祝你们新婚快乐”。
只是说完这句祝福,董艾米却已经泪流满面,即便如此,她还是说道,“请请给我一大碗喜酒喝吧。”
“以沫,酒。”赵守宪接过酒葫芦,近乎颤抖着说道。
王以沫反应过来,连忙跑到不远处,倒了满满两大碗酒端了过来。
“本来,我们也邀请了卫燃同志喝我们的喜酒的。”
董艾米说完,却是根本不等卫燃说些什么,便已经将粗瓷碗凑到了嘴边,咕嘟咕嘟的喝了一半,倒了一半,然后又接过第二个酒碗,同样喝了一半,倒了一半。
“你你接下来去哪?”卫燃问道。
“我准备回去了,这里已经没有我要等的人,也没有需要我去赴的约定了。”
董艾米说道,“我已经退役了,准备回华沙了,我的爸爸也在战争中阵亡了,我失去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两个男人。不过还好,维新给我留下了她。”
说着,董艾米自豪的展示着怀里那个不哭不闹的小丫头,“她的名字叫伊伦卡,我给她取的汉语名字叫董常春。以后等她再大一些,我会教她汉语,也会和她讲她父亲的事情,还有你们的事情。如果她愿意,她或许会来华夏看看。”
“是个好名字”
卫燃压下心头的酸涩赞美着,他早已经被金属本子教会了希腊语,所以他清楚的知道,伊伦卡这个名字其实就来自希腊语的“和平”。
只是,如今和平来了,那些争取和平的人却走了。
“等常春妹妹来了华夏,我们会好好招待她的。”赵守宪连忙说道。
“等她自己来了,我们把她当亲妹妹招待。”王以沫不断的擦着眼泪做出了补充。
今天本是他们两个大喜的日子,但却是他们两个最伤心的日子。
“会有那一天的,让我给你们拍一张结婚照吧。”
董艾米提议道,“然后我就准备回去了,以后我或许会在华沙开一家照相馆,也欢迎你们随时去华沙玩。”
“一起拍吧,我也正准备给他们拍一张呢。”卫燃说着,扭头看向了赵守宪和王以沫。
“拍,是要拍一张。”赵守宪最先应了下来。
“开心点儿”
董艾米劝解道,“你们爱的人活了下来,这是值得开心的事情。
这也是我准备以摄影师的身份拍下的第一张照片,我准备挂在我即将开业的照相馆里的,所以你们要开心点儿。”
“谢谢,谢谢你们。”
赵守宪用力擦了擦眼眶,又和身旁的王以沫动作一致的整理军帽,整理风纪扣,整理腰带和衣角,随后并排站在了一起,露出了国庆之日该有的灿烂笑容。
“咔嚓”
卫燃和单手举着相机的董艾米朝着赵守宪二人按下了快门,拍下了他们的笑脸,拍下了他们身后残破但是依旧蜿蜒的长城,也拍下了他们胸口的大红,拍下了他们脸颊止不住滑下来的泪痕。
“让我也给你们母女拍一张吧”卫燃看着董艾米提议道。
“那就拍一张吧”
董艾米并没有拒绝,只是仔细的整理了她的女儿董常春的衣领,随后将当初董维新抵押给她的老相机暂时挂在了这个小家伙的脖子上,随后又抽出手帕,仔细的擦了擦泪痕,接着又摸出一支唇膏补了补唇彩。
等她们准备就绪,卫燃艰难的举起了相机,同样以蜿蜒的长城和残破的碉楼为背景,朝着这对母女按了一下快门。
“守宪,你们也过去吧。”
卫燃招呼了一声,等赵守宪和王以沫分别站在了董艾米的左右,他也再次朝着他们按了一下快门。
“咔嚓”
异常清脆的快门声中,卫燃在扑面而来的白光中格外疲惫的吁了口气。
然而,随着白光消退,他却发现,自己并没有回到他熟悉的那个现实世界,反而来到了一座藏于山间的古旧中式建筑门口。
抬头看向门楣处,那里还挂着一个破旧的匾额,其上蓝底金字儿写着“无量观”。低下头,自己的脚边边放着行李箱。
无量观?那个道士军官?傅问爻?
卫燃心头一动,正要说些什么的时候,一个看着约莫20岁上下,穿着军装,肩头还挎着个包的小伙子从他的身旁走到了门口,轻轻拍了拍敞开的大门。
片刻之后,一个看着和他年纪差不多的小道士走了出来。
“道长同志,您好。”这名小战士干脆利落的敬了个礼。
“您也好,解放军同志。”这小道士甩动拂尘回了个宗教礼仪,随后这俩同龄人还握了握手。
“道长同志,我想向您打听个人。”
这名小战士问道,“您知道一个叫傅问爻的道长吗?您知道他的师父是谁吗?”
“傅傅.傅问爻?”
这小道士很是反应了一下,接着他却赤红了眼睛,“他他回来了?我师叔回来了?”
“他”
这小战士摇摇头,“他回不来了,他牺牲了,1937年,他就已经牺牲在冷口了,我我是来报丧的。”
“唉”
这小战士叹了口气,“进来吧,我师叔已经和其他的师伯下山十几年了,我师父早就猜到他回不来了。”
“道长,我能也进去吗?”
卫燃拎着行李箱走上来问道,“我也认识傅问爻,是是他的属下。”
“你是我师叔的属下?”这小道士瞪圆的眼睛里又下意识的燃起了希望。
“抱歉,他.他确实牺牲了。”卫燃歉意回答让这小道士眼中的希望又在眨眼间熄灭了。
“请和我一起来吧”
这小道士说着转过身,带着卫燃和那名小战士走进大门,走到了一座偏殿里。
片刻之后,一个拄着拐杖,看着约莫五六十岁的道士走了进来,“我师弟他回来了?他”
那名小战士敬了个礼,“我送傅问爻同志回来了,抱歉,他他牺牲了,1937年,在冷口。”
“唉!”
这位道长叹了口气,扭头看向那名年轻的小道士,“去烧水泡茶吧”。
“是”
这小道士躬身应了,转身走出这间偏殿,并且从外面帮忙关上了木门。
“我其实是受人所托”
那名小战士歉意的说道,“抱歉,我.我从来没见过傅问爻同志。”
“你没见过他?”
卫燃看了一眼这名小战士,“你你从哪知道他的?”
“金陵”
这名小战士在说出这个地名的时候,几乎和卫燃同时打了个哆嗦。
“你你.你是从.从金陵活活下来的?”卫燃腾的一下站起来,抓住对方的手腕难以置信的问道。
“是”
这名小战士在嘴里蹦出这个字的时候,却已经赤红了眼睛,“我叫徐知秋,我”
“徐知夏和你是什么关系?”
卫燃直勾勾的看着对方,他甚至听到了自己剧烈的心跳。
“是我亲姐姐”
和卫燃对视的徐知秋显然知道他想问什么,“1938年1月,金陵金陵大图沙。徐家.徐家只有我活了下来。”
“他们.”
“我姐夫我姐夫郭修齐,把我和我姐姐藏在地窖里,他杀了.杀了9个鬼子,弹尽,战战死了。”
用力做了个深呼吸,徐知秋继续说道,“我姐姐我姐姐不愿受辱,被鬼子发现的时候,用手榴弹自.自杀了。
我姐夫去杀鬼子前嘱咐我说,如果
如果活下来,等战争结束之后,让我去冷口寻傅问爻的尸体。
火化之后火化之后送来无量观,对不起,我.我来晚了。”
说着,早已泣不成声的徐知秋抹了抹眼泪,打开他的挎包,从里面拿出了一个骨灰坛子递给了那位道长,“我我姐夫没来得及和我说傅问爻的事情。
只说让我去哪找傅问爻的尸骨,火化了送来这里。”
“当年,我师弟问爻和我另外五位师弟五位师兄,还有两位小师叔一起下山去打鬼子了。”
那位道长叹息道,“我天生腿有残疾,去了也是累赘,这才留下来看守山门照顾师傅,只是只是唉!”
“傅问爻在冷口的时候指挥大家战斗,身先士卒,杀了不少鬼子。”
卫燃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他的行李箱翻找着,最终找出了一个布口袋打开,“他负伤之后,冷口沦陷,他不愿拖累大家,自杀了,这是这是他当年留下来的一些遗物。”
“哗啦啦”
伴随着清晰的碰撞声,一颗颗带着包浆的嘎拉哈和一个小沙包砸在了桌子上,那位腿有残疾的老道士却也已经老泪纵横,从怀里同样摸出了一颗嘎拉哈放在了桌子上。
“我们师兄弟12个,都是师父捡来的没人要的穷苦孩子,从小在这山里长大,从小就由两位小师叔照顾着。”
这位道士说着,已经熟练的抛起一颗嘎拉哈,又从桌子上快速挑中两颗嘎拉哈抓在手心,并且接住了抛起来的那一颗。
“这14颗嘎拉哈,我们师兄弟每人都有一颗。师叔们不比我们大多少,他们也各自有一颗。
那时候,我们只要聚在一起,无论是谁和谁,都会掏出自己的那颗嘎拉哈凑在一起,只要师父不发现,就能在这无量观的各个犄角旮旯玩上整整半天。”
一次次抛起嘎拉哈的道士自言自语般的回忆道,“临出发前,师叔说,大家都拿好了这嘎拉哈,谁要是回不来了,就把嘎拉哈带回来,说我看见这些嘎拉哈的时候,他们就回来了。”
“哗啦”
这位年过半百的道士终于没有接住抛起来的嘎拉哈,就像他没能忍住他的眼泪,没能忍住看向门外的道观,“九一八之后不到一个月,他们就出发去打鬼子了。这一晃,小二十年了,却不想.终究是等到了。”
说着,他颤颤巍巍的拿起了那枚小沙包,“我问爻师弟在卜卦上颇有天赋,他在出发前就给大家算了一卦,这一卦的解语就藏在这沙包里了,他说要等回来再看,还点名让我来拆开。”
说着,这位哭的像个孩子一般的道士已经用力撕开了沙包,让里面的黑豆和红豆撒了满满一桌子,也露出了一个仅仅只有指节大小的竹管。
拿起挑灯芯用的火针从这根竹管里捅出一张蜡封的纸条,他将其小心翼翼的展开,淡黄色的纸条上,却只用红色的朱砂写着几行龙飞凤舞放浪不羁的毛笔字:
拆此锦囊时,虽手足尽断。然日寇已败,华夏终将破旧立新,重回寰宇之巅。
师兄切勿神伤,当痛饮三大碗。贺,
战火尽熄,百姓乐业,天下太平!
这大概是倒数第三个故事了,也是这本书动笔之初设计的正数第三个故事。
贺:战火尽熄,百姓乐业,天下太平!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