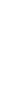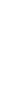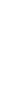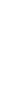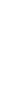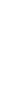三国:我刘辩,让大汉再次伟大 - 第295章 礼法岂是如此不便之物
第295章 礼法岂是如此不便之物
天子的话音方落,大殿內的气氛骤然紧绷,百官的態度立时呈现出鲜明的两极分化。
朝堂之上的派系,远非籍贯所能简单划分,还有诸多归类的標准,否则大汉十三州早就分裂了。
而如今在朝堂上,除了“小朝廷”和“大朝廷”之別,最为显眼的派系之別便是“少壮派”和“耆老派”这两股势力(qi)。
耆老派多是朝堂沉浮多年的老臣,行事作风难免沾染官场积习,加之岁月沉淀,年岁愈高,普遍求稳惧变,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颇低。
此刻多是眉头紧锁,面色凝重,显然对天子的提议並不赞同。
与之相对的少壮派则显得更有朝气和锐意,眼神中也跃动著认同和崇敬的光芒。
年轻的少壮派往往敢想敢干,对朝廷推行的新制接受度也更高,其中不少人对这位力挽狂澜扶大厦於將倾的年轻天子也多心存仰慕。
听闻天子竟筹谋將寿陵建於秣陵以节约民力,不使劳民伤財,心中的第一反应便是天子无上仁德。
方才朝臣们提出的镇压天子气方案,哪一条不是耗费巨大劳民伤財?
而天子为了不劳民伤財,將本就要修的寿陵定在荒芜偏僻的秣陵,这如何不是无上的仁德呢?
然而,即便是曾与天子並肩作战共抗今文学派的太常丞服虔,此刻也实在无法理解这惊人之想。
服虔霍然起身离席,手持板笏,躬身向前,额角隱隱渗出汗珠,急切劝阻道:“国家,自太祖高皇帝以来,天子寿陵无不是择址於京师附近。岂能……岂能选在千里之外的秣陵啊!”
“国家。”太常卿郑玄遥遥嘆了口气,缓缓开口,道,“焉止是我太祖高皇帝之后,自两周以来天子寿陵皆定於都城近畿,非仅为恪守礼制,也是便於后世君主祭祀奉养。”
郑玄的话语顿了顿,目光恳切地望向天子,他也无法理解天子这般奇思妙想,但与服虔不同,他的忧虑显然比服虔更深一层,不仅著眼於礼法,更牵掛著实际可能带来的负担,道:“譬如去岁,国家向世祖光武皇帝行献俘大典。若世祖陵寢远在扬州,国家岂不是要兴师动眾,千里迢迢奔赴扬州?如此,岂非反增劳费,更伤民力?”
刘辩看著二人,心中瞭然。
他能理解郑玄和服虔二人的劝諫,维护礼法本就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因此他並不会因此而恼,不过这也是他如此敬重郑玄的缘由。
“康成公方是真正的『儒』。”
刘辩说著,竟亲自走下陛阶,来到郑玄面前,伸手稳稳扶住这位正欲俯身再諫的老臣,不待郑玄反应,刘辩已挽起他的臂膀,拉著他便向陛阶旁走去。
郑玄猝不及防,被刘辩拉著,竟被按著坐了下来!
他惊得几乎弹起,好似这陛阶烫屁股似的,却被刘辩的手死死按住,一手按著郑玄的肩膀,一手指向他,目光扫过群臣,道:“尔等开口闭口皆是礼法如何如何,唯有康成公心中所思所虑,皆是百姓疾苦!”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若是为了维护礼法,而行不仁之事,那礼法还有何意义呢?”
刘辩这番话,算是堵住了那些仅以“不合礼法”为由的劝諫。
两汉虽说儒家学问分裂为今古文学派,也有著杂七杂八的弊病,但相较於后世那僵化歪曲得甚至畸形的儒学而言,还是相对开明与务实的。
“况且,礼法岂是如此不便之物?”
“子曰:『殷因於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如今朕愿意施行仁政,节约民力,对礼法稍作损益又有何妨?”
刘辩虽未曾参与过儒家士人们的辩经活动,但为了將寿陵选址定於秣陵,他实实在在地在东观查阅了大量典籍。
与过往由心腹臣子代为辩经不同,寿陵选址之事,许多支持的核心理由不当由臣子代为言说,譬如方才他决定修寿陵於秣陵镇压天子气。
尤其是当话题涉及到了天子气,那是国祚兴衰的大事,天子本人能宣之於口,谁敢妄言提出將寿陵修建在秣陵镇压天子气呢?
“至於康成公所虑后世祭祀之事,”刘辩嘴角噙著一抹温和却豁达的笑意,道,“太祖高皇帝的长陵远在西都长安,朕也未曾亲临,皆在雒阳的高帝庙中祭祀。同理,朕又何需后人远赴扬州祭拜?”
刘辩神情洒脱,仿佛全然不在意身后虚名般,朗声笑道:“后世儿孙即便不祭祀朕,断了朕的血食供养,只要大汉国祚绵长,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於朕而言,便已足矣!”
即便是郑玄这般儒家士人中最为开明通达者,也不禁愕然,他也未曾料到,天子竟对祭祀血食这等被视为头等大事的问题,也看得如此通透超然。
许多事,说著容易做著难。
生死之念,血食之重,常人尚且难以放下,何况一国之君?
昔年孝武皇帝早年也曾讥讽秦始皇轻信方士求仙问药,末了自己却深陷其中,晚年虽下《轮台罪己詔》反思“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却依旧难捨长生之念,宠幸方士炼丹服药。
这祭祀之事,这仁德之行,亦是如此。
三代以来,多少君王自幼习读“仁德”经义,执政后亦口称“仁德”,然其行其政又如何?
《古文尚书》有云:“非知之艰,行之惟艰。”
《左氏春秋》亦言:“非知之实难,將在行之。”
终究是知易行难。而眼前这位年轻的圣天子,却是在身体力行。
郑玄肃然起身,整理衣冠,向著天子庄重地深深一揖。
果然是不世出的圣天子!
所思所想,皆繫於大汉江山与万民福祉。
与天子的格局胸襟相比,他郑康成方才的顾虑,当真是太过狭隘了。
只是,隨著思绪翻涌发散,郑玄脑中陡然间有一道灵光闪过。
“知”与“行”?
这两个字如同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在郑玄的脑海中骤然盪开涟漪。
(本章完)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