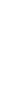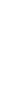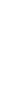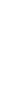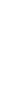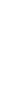红楼之平阳赋 - 第1166章 內阁对司礼监
第1166章 內阁对司礼监
帐內,
气氛陡然有些紧张,
富察真脸上的笑容微微一滯,隨即又荡漾开来,仿佛没听到那疏离的话语;
“夫人快人快语,那本旗主便开门见山,大汗的意思,重立草原秩序,和各部结盟,共谋长久之盛世!此番西进,夫人已经挡在路上,所以,本贝勒身后,有五万八旗子弟待命,若是夫人不答应,兵祸就在眼前。”
虽然富察真嘴上强硬,说的天乱坠,可他心里,也多是有些忐忑,大汗北地兵败回来以后,就病了一大场,身子亏空,虽说眼下见好了,后面好不好就难说了,尤其是几位旗主,相互看不过眼,几位贝勒年纪尚小,若是大汗出了稍许的事,女真又该何去何从,反正若是呼延含爭坐汗位,他是绝对不会罢休的。
抬眼看向眼前的草原明珠,早已经今非昔比,但此番使命在身,还是刻意加重了“五万八旗子弟”几个字,观察著乌雅玉的反应。
但见对方依旧平静,便话锋一转,充满诱惑:
“夫人,大汗念及夫人部族与我部族血脉相连,不忍兵戈相向,特命本旗主诚邀夫人,重归於好!只要夫人点个头,昔日恩怨一笔勾销,夫人仍是尊贵的固伦公主,您的部族將获封最丰美的草场!大汗甚至允诺,可与夫人共享关外通商之利。届时,汉地的丝绸、茶叶、盐铁,將源源不断流入夫人的牧场,而夫人的牛羊骏马,亦能销往四方。”
“夫人,汉人也说,当家做主,何苦寄人篱下,夫人莫忘,洛云侯,终是汉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今日他需夫人为其戍边,明日他强盛无匹时,焉知不会鸟尽弓藏?”
这番说辞,也是学了汉人那些秀才读书人的嘴皮子,都是一番话,换个说法,就能把死人说活,富察真说完,目光灼灼地注视著乌雅玉,期待著从她脸上看到一丝动摇或忧虑,若是乌雅玉还是熟视无睹,女真人这一回西进,真的是难了,那自己部落的前途,或许就在夫人身上。
帐內陷入短暂的沉寂,只有眾人的喘息声,两名捧著礼盒的亲兵手有些发酸,额头微微见汗,但面色上,不敢有丝毫变化。
乌雅玉缓缓抬眸,眼底没有富察真预想中的犹疑或恐惧,只有一片澄澈的笑意,意有所指;
“呵呵,富察真旗主,你所谓的血脉相连?指的是黄吉台当初逼迫我父兄战死后,可曾念过一丝血脉?前后都是他嘴上一碰,说的天乱坠,血债尚未清算,谈何『一笔勾销』!再者.”
乌雅玉眼神迴转,盯著富察真,他们二人也算是熟悉之人;
“至於你说的什么『重归於好』、『通商之利』?不过是镜水月,他今日许我重利,明日便能寻隙將我部族吃干抹净,再者,富察真,黄吉台丟了北地水草丰美之地,已经见势危的苗头,月氏人要是再度南下,侯爷假装看不见,那该如何,若是关外和月氏人结盟,女真人可还有活路。”
每一句质问,都像一记重锤敲在富察真心上,脸上的笑容彻底掛不住了,变得有些僵硬难看,他没想到乌雅玉看得如此透彻,这也是富察真忧虑所在,按理说,北地回来以后,应该休养生息,和洛云侯定下该盟约,既能安定部族,又能採买紧缺粮草过冬,谁知道,那群短视之人,想出来“北失西补”之策,蠢笨至极。
“夫人!”
富察真面色僵硬,硬著头皮也想不出其他言语,忽然灵机一动,汉人都说,狡兔三窟,若是还有著一丝情面在里面,自己是不是可以留下一条后路。
“夫人,有些话,自是不必明说,如今女真人各部,商议出来的事,就算有人反对,也算是螳臂当车,话说夫人於此,我富察真还真没有好好奉上贺礼,实乃惭愧,一但侯爷回来,若是侯爷有意,一切都好商量与我,也能全了当时候的情谊,夫人觉得呢。”
乌雅玉面色有些古怪,这些话里的意思,她是听出来蹊蹺,与我有意,而不是与女真人大汗有意,看来,富察真想两边下注了,想到他以往的做事圆滑,还真有可能。
“旗主果真是心思剔透,乌雅玉实乃佩服,若是这一回谈不拢,大汗能按兵不动?”
“这,自然是不可能,呼延含剴窃夫人已久,如今这么好的机会在眼前,成与不成,他都会按耐不住,所以,夫人还需要西撤,袭扰为主,只要夫人五万轻骑在外围,女真人勇士,必然不会尽全力攻城,倒是那些汉八旗包衣奴才,战力斐然,当然,洛云侯回来,暂且两说了。”
富察真没有来时候狡诈,说的都是实话,诚心诚意,多为以后留一条路,乌雅玉心中一动,面带笑容,
“还是富察真贝旗主敢说这些话,既如此,雅玉就不留大人了,此番用兵,早有定测,倒是富察额真,回去后万不得损耗太多兵丁,若有机会,辽南一地,可容不得那么多人。”
指了指南边,似笑非笑。
富察真立刻会意,抱拳行了礼数,就告辞离去,在大帐入口出来以后,上了马,匆匆离去,临回头的时候,寻见帐外的將校,依次入帐,心头一嘆,身后跟著的阿齐格问道;
“阿玛,您为何说这话,万一被其他人知道,”
只怕是祸事临门了。
岂料富察真冷笑一声,
“阿齐格,人活著才有一切,此番大汗大病过后,还不知能撑著几天,上三旗,以正红旗呼延含势力最大,若是他想要爭夺大汗位子,或者推举豪格入了汗位,我和瓜尔佳绝不同意的,那时候,只能兵戎相见,此番西征,必然会惹恼洛云侯,那时候。”
眼神闪过一丝异样;
“恰好乌雅玉和咱们也有个香火情,既如此,就要两头押注,可惜,汗帐精锐都在赫连臣手中,一直中立不出,唉。”
阿齐格满眼惊讶,阿玛所言句句在理,倒是风吹两头,怎么站稳才是主要的。
“阿玛,回去后,又当如何?”
“如实匯报,万不能走漏风声。”
“是,阿玛。”
就在富察真回汗帐的时候,平辽城下,惨烈的攻城战,一刻不停歇,汉八旗的兵卒,悍不畏死,攻城甚急。
关外战火纷飞,关內,却歌舞昇平。
京城,
养心殿內,殿內檀香裊裊,却驱不散那份沉甸甸的凝重。
窗外是京师初秋的午后,天高云淡,隱约可闻市井的喧囂,但这巍峨宫室之內,空气仿佛凝固了,关外烽火重启,关內又添了许多动盪,各地匪患猖獗,山头林立,年后运送的流民,也只有沿河的郡县好一些,但西北和西南腹地,依然是老样子。
巨大的鎏金蟠龙烛台尚未点燃,临窗户也未打开,殿內光线略显幽深,更衬得御案后,那位身著明黄常服的帝王面色晦暗不明。
武皇周世宏端坐於宽大的紫檀木御座上,指节分明的手指无意识地在光滑的扶手上敲击,发出几不可闻的“嗒、嗒”声。
面前的御案上,几份奏摺摊开著,最上面一份墨跡犹新,正是內阁重臣决议出来的奏疏,另一份,则是司礼监掌印太监陈辉,之前上的摺子,另有洛云侯临走,留下一份奏疏,亦是如此。
御案之下,气氛更是压抑。
內阁首辅李崇厚鬚髮皆白,肃穆坐在最前头,眉头紧锁,身后是两位同样神色凝重的阁臣,垂手而立。
他们对面的人,则是司礼监秉笔太监陈辉,身著蟒袍玉带,面白无须,身后侍立著几位、隨堂太监,个个屏息静气。
爭论已经持续了小半个时辰,此番前来议事,就是谈论徐长文最后的定罪,內阁和司礼监,各抒己见,互不相容。
“陛下,”
户部尚书顾一臣,再次上前一步,声音有一丝沙哑与恳切,
“徐长文一案,牵连甚广,诸多奏疏记录,多有实事,甚至於乃至……太上皇时期的一些旧例。今洛云侯张瑾瑜领兵北归,主审官员缺失,臣等以为,当暂押徐长文於詔狱,待洛云侯回京以后,再行三司会审,务求水落石出,明正典刑,此乃老成持重之法,亦显陛下仁德之君明察秋毫。”
顾一臣的话语稳重,实则是用了一个拖延法子,既然主审接连缺失,总归是无法再审,许多事,既然有了苗头,何必急於一时,这样一来,等太上皇消了气,自然是有法子解决。
话音刚落,司礼监的人,怎会让步,马飞阴柔的话语响起;
“顾阁老此言差矣!陛下明鑑,国法岂能因一人而废弛?洛云侯北归,是因女真人西进,战火重启,战端一开,何时结束,尚且不知,洛云侯若是一直不回来,这案子怎可久拖,然则太上皇虽静养龙体,但因何缘由,都是徐长文眼中没有君父,不知尊卑,司礼监、三法司会同內阁,当初所议『秋后绞刑』,已是念及天家体面,未加凌迟。此议,不可更移!”
马飞此番话,就是为司礼监爭权,商议好的罪责,总不能內阁怎么说,就怎么改吧,这样一来,还要司礼监何用。
“马公公!”
顾一臣身旁站著吏部尚书卢文山,终归是插了一嘴,道;
“话不能这般说,都说是非曲折,不辩不明,徐长文狂妄,自有他的罪责,此番审问,尚有许多不明之处,有的案子结了,有的案子,还在审问当中,再者,洛云侯回关外,老夫以为,战事必不能持久,当知道关外苦寒,可不是嘴上说说,刚入了秋,要打也没几日了,再等上一段时间,又该如何。”
虽然看似打了圆场,可是破了司礼监定下的秋后问斩,这样一来,案子就能拖到明年了。
其中的意思,在场人也听的明白,陈辉冷哼一声,显然不认同:
“卢阁老,您是管著吏部的,此议若准,国法威严何在?徐长文的案子,早已经审完,会同当日议罪,尔等也没有说不准,隔了几天,就这般改口,哪还有信宜所在,司礼监以为,当依三法司所议,徐长文狂悖之徒,秋后斩立决,抄没家產,其朋党徐东流放!”
陈辉说完,但心中多有些慌乱,可落子无悔,怎可退后一步,想到昨夜司礼监眾人合谋,若是退缩,司礼监威信扫地,再无迴转之力了。
“陈公公此言,才是轻重失当!”
一直不吭声的兵部尚书赵景武,忽然开了口,眾人面上都有些诧异,毕竟內阁决议的事,赵尚书之前没有入阁,这些事也与他无关,此番开口,有些古怪,就连坐在上首的李首辅,也微微睁开眼,看了过去。
赵尚书出列,躬身一拜,
“陛下,此番徐长文议罪,本不该老臣插言,但老臣听了诸位阁老,和几位公公的话,都觉得有道理,而徐长文罪当诛,內阁从未否认!至於量刑轻重,自有陛下圣裁!所爭者,唯时也!想要此案使內外心服口服,杜绝悠悠眾口之非议!確有困难,但臣要说的是,南边来了兵事的摺子。”
赵景武从怀中拿出竟有一沓的摺子,捧在手上,道;
“陛下,荆南各郡,府军已经开始集结,另有几位王爷府上长史上书,组建剿贼大军,集结的兵马,则是在荆南樊城,凌河以北之地驻扎,又有南方昌云,寧南,南河三郡急报,贼教大军忽然从岭南北侧南下,席捲南方,怕死贼教死灰復燃,划地为治。”
此言一出,堂內顿时气氛凝重,刚刚在京南镇压贼教,转眼死灰復燃,这里面,是几位王爷的布局,还真有其事,尚未可知。
眼见著正事没议论完,又添一事,武皇的眼神,更显阴霾。
“咳咳,赵尚书,此事暂且稍后,既然你赞同案子延后,老夫倒也有话要说。”
李首辅扶著椅子扶手,咳嗽了两声,
“陛下,徐长文罪有应得,此番压在牢里,插翅难飞,但临近秋闈,恩科在即,恩典还要给的,可太上皇心意难消,既如此,这些摺子,不如转呈太上皇,都说上天有好生之德,太上皇怎会为难与他一个小小县令秀才,老臣虽然年迈,可有些事,君父一道,父子和儿子的事,忠言逆耳常有,也不可有左右之蔽。”
话说的不快,殿內眾人听得真切,文臣一侧,皆是点头同意,只有陈公公不甘心,
“左右之蔽?首辅大人慎言!”
陈辉的声音陡然变得冰冷如刀,
“司礼监秉笔,乃代陛下批红!所行所议,皆仰体圣意!首辅大人此言,莫非是影射陛下不明?”
转身向御座深深一躬,语气转为悲愤:
“陛下!老奴等侍奉之忠心可昭日月!徐长文之罪,桩桩件件,铁证如山,早一日明正典刑,便早一日肃清流毒,安定人心!若是拖得久了,天下人议论纷纷,贼教蛊惑人心的手段,诸位大人也不是不知道,內阁诸公一味拖延,天下哪有这般道理!”
陈辉的言语极其犀利,可谓是句句如刀剑,但李首辅什么样的人没见过,轻轻摇摇头;
“陈公公,天下诸多事艰难,怎可一味追著此事不放,兵部那边的奏疏,既然已经收了,就说明贼教不死心,南边三郡靠海,民风彪悍,不是易於之辈,挡不住的话,只能靠荆南几位王爷用兵了。”
毕竟南方大军,尽皆在蜀地还有江南京南一线,若是几位王爷不动兵,只能靠南王郎平率军平叛了,国事艰难,不过如此。
幽幽一嘆后,武皇周世宏的手指,也停止了敲击,抬起眼,那双深邃的眸子,缓缓扫过阶下的重臣们。
关外战火重启,洛云侯回关外,京营和府军,都在重建,尚需要时间,南方各郡动盪不安,贼教復起就在眼前,这一幕幕的事,都在他脑中飞速旋转、融合、权衡。
至於眼前的案子,比上这些,確实无关紧要了,但太上皇那边,还需要一个台阶下,司礼监的人,能体会圣意,可惜,走的步子太著急了,
“够了。”
两个沉闷的字,如同冰水浇头,让李彦明和陈辉瞬间噤声,躬身垂首。
殿內落针可闻,
周世宏的目光先落在陈辉身上:
“陈辉!”
“老奴在。”
陈辉立刻答应,快走几步上前,躬身更深。
“你说徐长文罪证確凿,当速杀以儆效尤,以正国法?”
周世宏语气平淡,看不出喜怒,陈辉遂心中胆战心惊,但也只能硬著头皮点头回道;
“是,陛下!案子早已经审的清楚,虽然徐长文不贪,但以此邀名,无非是想逼宫,名留青史,若是后来者有学有样,国將不国,此獠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正视听!”
周世宏微微点头,目光转向李首辅,问道:
“李卿。”
“老臣在。”
“你说此案尚有关键处,需內阁和刑部釐清,仓促定案恐有疏漏,亦虑及寒了朝廷文武之心?”
(本章完)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